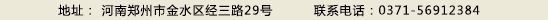坝河文萃寻野菜渡春荒
作者:来宝胜
那些年,农户人家粮食大多不宽裕。农历二三月,田间地头的庄稼绿意正浓,麦子拔节抽穗扬花儿,早熟的胡豆豌豆没饱米儿。青黄不接的时节,最熬煎人。为渡过春荒,妇女和小娃们找野菜充饥。
提着竹笼寻遍山坡野地的角角落落,半蹲着摸摸索索拔野菜。嫩绿的鹅儿肠铺满麦地空隙,荒芜庄稼是头牌子,死招人讨嫌,一般是拔了喂猪崽。粮食紧张的年份,鹅儿肠被洗净剁碎,和包谷篸煮成绿哇哇的稀糊粥,充作人的饭食。阳坡有不少蒿子,能吃的只有白香蒿。揪下嫩叶淘洗干净,与黄豆磨成的豆浆煮熟做成懒豆腐,放点盐搅合一下当饭吃。开始觉得清香,口味新奇,两三顿下来,只感到堵塞喉咙,令人哇哇作呕。就是这,硬着头皮也得吃,渡命要紧呢。
庄稼地、土路边,荠荠菜随处可见,一扑棱子散开贴在地上,连根剜起洗净,拌拌汤、煮糊粥,一股脑倒进去煮了,一筷子起来,连麻带芡的,连汤带水囫囵吞咽几碗下肚。晚饭汤汤水水,肚子倒是胀得鼓圆,睡觉净做梦,小娃子十个有八个经常尿床,每天一大早,农家院坝边的晒衣杆上,搭着印满尿花圈圈的铺盖,尿床的小娃子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。
阳坡的野地边有野小蒜,小心地从土里拔,或是用细木棍儿剜,一段儿白的带着小指蛋儿大小白疙瘩,有点绿波仙子的模样,是春季里最好的野菜。缺菜吃的季节,切碎小蒜和干辣椒放很多粗盐炒了,一小碗很咸的辣酱,是唯一的下饭菜。小蒜味道再好,也只是配班儿,就那么一丁点儿,不能当饭。
刺芽菜的嫩白根深深扎在地里,开春后密密匝匝冒出来,一片一片的,叶子上的细刺有点扎手,好在农家娃们很皮实不怕扎,照例拔了。如果当菜吃,开水燎过窝成酸浆水,去掉刺芽菜略微清苦的味道。水田边的淤泥有不少水芹菜,似乎带点腥臊味儿,是农家人最喜欢的野菜,平时无人问津,春荒时节却翘得很,村姑孩童三三两两提着竹笼,野芹菜被拔了一茬又一茬,泡酸浆水凉拌。五六月份新粮食接上茬,野芹菜的身份变得低贱起来,再也无人理睬。
农家娃子那个不认识几十种野草野草呢,这不,山坡野地随处可以找到能吃的野菜。刺椿芽浑身是刺,那才叫一个扎手,趁着嫩嫩的还没散鳞儿,要么砍倒,要么用木勾搭子钩过来掰掉嫩芽,开水燎了当菜吃,味道有点苦,有点涩。某年到昆明出差,朋友说晚上让我尝一道天然环保的养生菜,待端上桌来,诶,不就是小时候常见的刺椿芽子么。那盘菜80块,只令人心疼,又感到几分矫情。据说一些山里有经济头脑的人把刺椿嫩芽掰了燎熟,真空包装,送到大城市的餐桌,竟然奇货可居呢。
清明前后,薇菜冒出带绒的头,有叫蜷秧、鬼脑壳的,嫩得能掐出水来,吸引村姑碎娃们趋步而来,刚掐过一轮儿,第二天又冒出新的,掐呀掐,似乎没有个完了的时候。“采薇采薇,薇亦作止”,薇菜绽开嫩绿的芽尖儿,采薇的人儿采了一把把。《诗经》中描绘的采薇场景,今人已不能体会其浪漫有趣的场景。薇菜掸过水,晒成干菜,最好是和了腊肉炒,油滋滋的肥腊肉才能润透干翘翘的薇菜,耐嚼,有回味儿,只是那年月农家那有那么多腊肉来炒,偶尔吃点腊肉炒蜷秧简直是过生日。
蒲公英土名儿黄花庙,如今成为人们喜爱的一道凉拌菜,什么清火败毒、祛病健身、预防癌症等,被传得神乎其神,当年就是一种猪草。鱼腥草带着令人恶心的怪腥味儿,打猪草都嫌弃。记得小时候和伙伴们打猪草只顾玩耍,天黑了猪草笼子还空着,害怕家长训斥,慌里日饺子地拔扯一些鱼腥草滥竽充数。如今倒好,每年春季,菜市场上有鱼腥草卖,一小把把儿就一两块,偏有人要买,当八金宝儿似的,给人以风水轮流转的恍惚。
一种名为六月嫩的野菜,叶片尖牙齿状,有叫还阳草的,几寸长的茎蔓铺在地上,阴坡的地边最多。薅草时锄头下去,砸成短节节儿,就是不得死,天天有人去拔,却拔不干净。叶片儿略微钝圆的可以燎过水泡酸菜,叶齿尖细点的苦的难以入口,又叫“药六月嫩”,缺吃的人户照样拔了吃。
寻野草,渡春荒,令人回味绵长。我仍爱吃的野菜还是六月嫩,算是童年生活延续至今的例证了。
图片:摘自网络。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chenzhisheng.com/qcjz/24505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