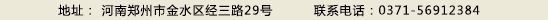碧涧羹丨古人如何吃芹菜,让杜甫忘记烦恼的
近日读《山家清供》,见到一道很时令的菜,是关于芹菜的。
二月、三月时,春寒未尽,芹菜凛寒而生,趁新鲜采来洗净,用热水焯过。之后“以苦酒研芝麻,入盐少许,与茴香渍之”,即加入芝麻、茴香,调少许醋和盐,可作腌渍菜。
想来与历史上的名菜“醋芹”,堪称“一味相承”。“醋芹”据传是一道小菜,芹菜经过发酵,佐以五味,酸咸开胃,清香扑鼻。刻板严肃的宰相魏征,平日里“无所好”,很难“动情”,却唯独在吃醋芹的时候,“欣然称快”,而能见其真态。
芹菜清香迷人,色泽更是赏心悦目。作为书中记载的第二道菜,“碧涧羹”的名字诗意盎然,可见古人在吃这件事上,有足多情致。这道菜的命名其实源于一位敦实稳重,忧国忧民的诗人——杜甫。那是在天宝年间的初夏,杜甫与友人出游,行至长安城南少陵原下,走入一片山林胜境。碧潭百顷,微风阵阵,低垂的树枝上挂着野果,葱郁的叶片遮天蔽日,林间清凉,莺声婉转。
正是在这样充满野趣幽情的环境里,杜甫品尝到了这道“香芹碧涧羹”。一碗羹汤,十足清淡。菜色淡绿,如明净的玉色,细碎的茎叶悬在汤水中,若隐若现。这道菜原就不在于口味,而在于颜色。
香芹亭亭,清爽淡然,犹如青碧的山涧,泉水淙淙。这样一口温馨的汤,明明是人间烟火,却令人心思澄澈,置身事外。在这个时刻,时间缓慢,四周幽静,平日长安城里的红尘滚滚,宦海沉浮,仿佛已经远去。
这道菜的形与神,正好应了《山家清供》里的描写:既清而馨,犹碧涧然。自杜甫之后,很多文人对清新的芹菜爱得深沉。南宋时期,有一位不太知名的词人高观国,曾留下这样一句评价:“碧涧一杯羹,夜韭无人翦”。为了喝上一杯碧涧羹,夜里已无人再去收剪韭菜。
现在听来很有些古怪,可是在古时候,人们形容菜之美者,便有“春初早韭”的说法,因为家家门前种植韭菜,更是留下了“夜雨剪春韭”的典故。春天正是味蕾大动的时节,万物萌生,想要吃到新鲜的好味,不得不抓紧时间。在这个时候放弃了“春韭”而转投“春芹”,如此便对比出了这一道碧涧羹的魅力。有趣的是,这句“夜雨剪春韭”正是出自杜甫笔下,不知道高观国的这一句对比,是有意还是巧合。
现在碧涧羹的做法已被改良。先在锅中炒香干贝,爆出鲜味,炖汤时再加豆腐、笋丝、姜丝,芹菜虽是主味,但也要放低身段,与其他食材配合。乍看是清汤白水,其实暗藏珍馐,干贝是海鲜,笋丝是山鲜,豆腐看似家常,家庭条件不好的年代,却被称为“素肉”,也是佳肴。相比之下,这道汤已不同于古时寒酸,可惜味道虽然更加丰盛,意趣却略显简朴。
碧涧羹至美,正是美在清寒。
相比于鱼肉荤腥,以干贝、竹笋调味可以算作高雅,但文人仕子的风骨,“一箪食,一瓢饮”,愈是清贫,愈是清高。“孔子食藜羹不糁”,陆游曾以“藜羹”自勉,自古以来,汤食亦可象征气节。
如今碧涧羹少有人耳闻,不能成为家喻户晓的家常菜,或许是因为寡淡,可它清清白白的质地,其实是一种失传的意境。
许多人读陋室铭,皆以开篇“山不在高、水不在深”两句千古留名,可我看来,最妙的反而是这一句: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。平仄音韵和谐,一个“青”字,立刻给房间的景致加了滤镜。陋室不苦,反而有几许浪漫。青莲、青竹、青灯、青蔬、青青子衿,一抹深深浅浅的绿,在诗词曲赋里明明暗暗,是国人骨子里的含蓄和淡泊。
诗经中说:“思乐泮水,薄采其芹”。“芹藻”“采芹人”多指代有才学的秀才。后因为《列子·杨朱》中一个故事,又多了一层引申含义。有人以茎芹为美,献于乡豪,那乡豪吃过后却“蜇于口,惨于腹”,简直受了苦头。因此“芹”成了一个微薄谦辞。浅薄的建言,便是“芹献”“芹曝”,芹曝终怀野老心。自己微不足道的心意,则是“芹意”“芹诚”,尚有献芹心,无因见明主。
辛弃疾曾著《美芹十论》,堪称“雄有万卷,笔无点尘”,从审势、察情、观衅、自治、守淮、屯田、致勇、防微、久任、详战十个方面言抗金大计,慷慨卓然。于是美芹连同悲黍,有了忧国忧民的色彩。
人或许如芹菜卑微,而心志不减,初心不灭。这或许才是自然语言里更深层的含义。“芹泥”指春燕筑巢时衔来的一点泥。芹泥雨润,燕落芹泥,风雨飘摇的日子过去,总会见到春阳。经历过起伏,会更懂得平凡人的“芸心芹意”——简单轻松的“绿色心情”。
到了近代,因为“芹”音同“勤”,民生在勤,而芹茎中通,通达顺遂。芹菜多了一些民间吉祥的寓意。新春佳节时,还会以年华组盆的形式出现在广州的花市上。上世纪中旬,许多女孩都有小芹、秀芹的闺名,也是取其朴素而易于生长。
“一芹之微”,芹菜是如此卑微渺小、毫不起眼的植物。甚至曾经赋予它的种种象征都已随风散去。可是总有一些感知力,潜藏在我们的血脉中。
读到这些典故的时候,会恍然一惊,再会心莞尔。如同黄庭坚在午寐时吃一碗芹菜面,而寻回了前世的记忆。中国人对美的感知,其实就在每一道吃食里,等待我们重新找回。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chenzhisheng.com/qccp/24593.html